《八佰》在影院复工后拿到了第一个十亿票房,时尚先生 Esquire 与导演管虎在他的工作室见面,给他和他电影里出现的动物们拍了组大片,还与他聊了聊他这几年专注创作的电影和电视剧。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:时尚先生(ID:esquirecn),受访者:管虎,编辑:暖小团,摄影:尹超(SUPER STUDIO),采访撰文:浩川,头图来自:时尚先生Esquire
我自打记事起到十一二岁,脑子里的画面永远是在北京的胡同里一个人跑着,就后海、鼓楼那一带,现在还特别熟。我爸妈当时都去劳动改造了,一个在青海,一个在北大荒,可能一年见一次,我被寄养在一个邻居的爷爷家。人家孩子都有家长管,我没人管,野惯了,逃课天经地义,跑这儿跑那儿特自由,那个经历对于我是很难得的。
小时候我性格太皮,是别人眼里的“坏孩子”。从小我的个子就比别人高一头,这在当时不是优点,是被嫌弃的,因为异于常人。我曾经渴望有机会能融入集体,但也怪了,怎么都融不进去。
王小波有本小说叫《一只特立独行的猪》,讲一只不服管束、整天窜墙上房的猪,我就觉得跟我特像。一个男孩子,从母体内生出来,在长大过程中,他要没点混劲儿那才见鬼呢,后来这股子劲儿没有了就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被摁住,并且大家都觉得没有这种气息是对的。拍电影让我有机会把身体里弥漫的这东西表现出来,我有兴趣分析一下这些异类,并不觉得这有多高级,但是得有人去这么做。
剧本创作的想法都不是突如其来的。我从来都不明白什么是灵感乍现。它更像是一种隐隐的一直藏在心里的叙述感,跟个人的情趣、爱好、履历,性格都有关系。像《斗牛》《杀生》中的人物其实都有我身上的影子,可能是在疏解我童年成长经历中巨大的孤独感。我比较喜欢描述那种在大的绝望环境中,个体生命的体验,最重要的就是他的生命力之旺盛,几乎是动物性的。
到 13 岁父母回到北京我才搬进北影厂大院,周围都是大明星,环境立马不一样了。大明星的孩子也对电影特别了解,能看到很多外面看不到的电影。我一个“胡同串子”突然到那个环境,会有些自卑,但是每次看电影,情节发展和结局都是我猜得最准,慢慢找回点自信,开始喜欢讲故事了。

历史是我中学时唯一感兴趣的科目,包括课本上那些小字注解我都看得津津有味。中国近代史上的战争我如数家珍,考试根本不用背,后来高考 100分的卷子我考了 98,是海淀区艺术类考生历史最高分。
我本来想考摄影系,因为那会儿我总拿着相机乱拍。艺考前我爸带着我去见电影学院的老师,我当时说话吭吭哧哧,脸红脖子粗,说不出一句整话来,人家就说这孩子是不是跟人交流有问题啊,要不然试着讲个故事?我一下就好了,能讲得特顺利。学院的考题一般是出个题目,让你在很短时间内编一故事,那老师就建议我考导演系,现在想想这一段,我真的应该好好谢谢当年那位老师。
上学时,电影在我心中一点都没有高不可攀,小孩心理承受力差的同时也容易把自己拔高了。当时就觉得世界都是我的,别人都不在我眼里,都等着我出来呢,就类似这种心理状态,现在说有点可笑,但当时确实是这样。
我毕业后是电影行业最不景气的时候,厂长背着拷贝满世界去卖,电影院都改成台球厅了,那时候的人们没有买票看电影的习惯。我其实有拍电影的机会,一个低成本的,拍完没有任何动静,扔在片库里就完了。那时候我们都会对从事这个行业产生怀疑,生活都无着落,真有点慌了。我跟路边要饭的说你别跟我要,咱俩其实是一样的。
后来通过拍电视剧,整个生活的局面好了一些。从我拿着剧本敲门求人给我点钱,变成我坐家里人拿钱来找我,可以说是打下一点“江山”。电视台也信任我,再往下走的过程中形成一些习惯性的东西,我就反思自己,觉得还是得回到电影。这才有了之后的《斗牛》《杀生》。
《厨子戏子痞子》是我第一个票房上亿的片子,有点实验性,大着胆子耍一下,拍那片子的出发点其实有点斗气的意思。有一年上海电影节,办了一个什么论坛,有我、娄烨、王小帅,我们几个人坐上面还论呢,底下有个记者一边拍一边说:哎呀,中国电影最不赚钱的几位导演全在这儿了!把我气坏了。
没人跟钱有仇,但电影对我们来说还有文化属性。他非要提这个,我那小孩脾气就上来了,既然你这么说,那我就拍个赚钱的给你看看呗。于是我就弄这么个像密室过关似的故事,我就是想告诉他们,商业电影我也可以做,而且会做得很好,只是愿不愿意去做。

《老炮儿》可以说是我个人表达和商业价值达成平衡的一部作品。电影上映后,我看到有评论说它有文艺片的气质,到底是文艺片还是商业片,这对我不重要,我关心的是作品究竟带了多少作者属性在里边。
你愿意追寻好莱坞那个类型化,但不是去信服它,类型化套路在美国、欧洲是成功的,你凭什么告诉我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这就是对的,中国电影有没有可能做自己的逻辑,自己的商业属性。作者性是我在每部作品中一直在尝试的,《老炮儿》算是尝试成功的,反正就是不能轻易从众,争取有一些引领。
创作这件事是挺需要自信的,确立信心不是你在家一拍脑门子强行说我是对的,是靠外界反馈慢慢的构建成的,内心的柔软只能自己去克服。每每面临质疑的时候,我采取过很多方法,不闻不问,躲起来,强行不看评论,但都不行,半夜又偷偷打开看,还是得面对,你一定会经历一些大锤子、大刀子一样的沉重打击,那怎么办呢?做这行业的代价就是这样。
我爸其实是个老八路。十三四岁时在山东农村生活,他说那会儿每天从他窗户后边过军队,一会黄军装,一会灰军装,打枪打炮的。家里也没饭吃,快活不下去了,他就找了双鞋,翻窗户跟着一支军队跑了。
那是罗荣桓将军的 115 师,刚进山东,后来罗荣桓将军北上到四野去了,他就留在陈毅的 7 兵团 35 军,跟着部队一直打进北京城,算是资格很老的八路。有一年国庆阅兵,说过去了一个方队,就是当年的原罗荣桓 115 师,老爷子立马特激动,把参军的经历跟我详述了一遍,我听了也很感动,我感觉爱国主义是长在很多人骨子里的。

拍摄一部战争片是很多男导演的夙愿,因为战斗是男人身体里一种天性。我对中国近代史历次战争都很熟悉,这次拍摄《八佰》,之所以要选择淞沪战役中的四行仓库保卫战,就是因为这场战斗在世界战争史上是前无古人、后无来者的。
苏州河以南是租界区,日军枪弹不能打过去,所以就形成北岸枪林弹雨、尸山血海,而南岸继续歌舞升平的奇观场面,老百姓可以吃着饭、喝着咖啡在五十米外观看这场战斗。今天我们总提什么“网红直播”,那才是世界上第一场被“直播”的战争,路透、法新、美联,世界各国的军事观察家全来了,各路长枪短炮架在南岸拍摄,最多的时候有 3 万人围观,很多华人摇旗呐喊,为北岸的战士鼓气,而在外国人眼里几乎成了一场表演,这很适合用电影手段呈现。
更重要的,我是想要说自己的一点责任感,这不是什么酸词。一个能够轻易忘却自己苦难的民族,这个民族能在前进中吸取教训吗?我觉得很难。那一辈人死了就忘了,这哪儿成啊?所以电影除了商业属性以外,还有文化属性,达成一种提醒功能,拿出来大家讨论,让后边更多人知道,我觉得这是一件有功德的事。
以我的认知,电影中人物是第一位的,其次才是故事。我欣赏的战争片都不是太常规类型的,像库布里克的《全金属外壳》,或者泰伦斯马力克的《细细的红线》,它用战争作为一种载体,叙述战争中个人的生命体验,这是我比较喜欢的。所以《八佰》不是战争类型片,只是有战争元素,它表现的是中国人身上原本该有的一些光辉的东西,平常被磨灭了,但在绝境中给逼出来,这就跟今天的人有关了。

我们考证了很多史实,但没有一个是真正描述四行仓库里那 4 天到底发生了什么,都是从外围看到的。所以我们把景物真实的还原,让演员长时间军事训练,制造身临其境感觉,摄影机跟着他们走一遭,看会发生什么,所以这是一次《清明上河图》式的散点叙事,没有男女主人公,不讲故事,塑造了一组群像,这在创作上其实是特别冒险的,也是拍这个戏最大的挑战。
《八佰》无疑是我职业生涯目前拍摄的最大规模的作品。拍摄的过程中,我一直在和主创商量,能不能咱们回到大学刚毕业时的心境,恢复那种拙朴劲儿,像寿司大师做手工活那样,一点一滴地做一件特笨的事。
年轻时我们都会沉迷于花哨的手段,希望别人看到我的聪明,但是随着见识、修为的提高,人都会越来越稳定、沉下来、去关注一个人、一件事,你会发现老实地画一幅素描才是最考工夫的,就是往臻于化境那上头再走一步,这是我现在的乐趣所在。

做导演首先需要才华,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有承受力,就那股韧劲儿,耐摩擦能力,如果只靠热情和梦想来支撑,在我看来走不了三步就得倒。我接触过一些年轻导演,梦想很强烈,但是一遇到困难马上折,梦想和妄想一线之隔,那个分寸很微妙,这是我目前最大的感受。
外界说我拍《八佰》是“十年磨一剑”,这有点儿美化我,其实我中间还干了很多别的事。只是十年前说有机会拍这个,开始写剧本,但是想简单了,钱、资源还有一些其它因素都还不成熟,只能放下。
后来和华谊合作,本想在原址上拍,没批准,找不到场地,剧本又重新改。终于找到地儿了,要搭一个四行仓库,不想工程收尾赶上南方雨季,预计的开机日期不可能实现,演员所有合同作废,再停。最后真拍起来,遇到的困难还是远远超出我的预期,好几次也会产生质疑,到底值不值得耗费这么多时间、精力做这件事,最后还是坚持下来,没什么可抱怨的,我就是为了克服这些困难而生的。
关于电影,现在大家基本一聊就是票房占比,大数据分析,这个档期里还有什么电影,但这其实都跟电影本体没什么关系。电影的商业属性是与生俱来的,但不是唯一的,还有很多种功能,现在中国电影在资本的裹胁下,可以说淡失本体。50年后回头看现在,还能留下几部什么电影,谁也不会管你当时的票房占比、档期,重视的只有作品本身。

资本泡沫是一个行业高速发展必然产生的,2000年初韩国影坛经历过,日本70年代也经历过这一套,犯不上批评,我觉得这不是谁的责任,是时代的责任。过去我们的偶像都是崔健、 Bon Jovi 、诗人、画家,现在小孩都想成为马云、马化腾,谁也改变不了什么,仅仅等着它过去就行。
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水落石出的过程,现在已经看得很明晰了,你弄一千个明星演这戏也火不了,观众会越来越挑剔,这都是朝好的方向在发展。好的创造、好的作者是宝贝,还是会有明白人在适当的时候,做一两个能留得下来的东西。
我现在已经变成了20年前我最讨厌那类人,所以学会了从别人的角度看问题,发现人家不见得是你想的那样。现在我不会较着劲做什么事,会有妥协,但尽量不失自我,进入到人生的另外一个轨道。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:时尚先生(ID:esquirecn),受访者:管虎,编辑:暖小团,摄影:尹超(SUPER STUDIO),采访撰文:浩川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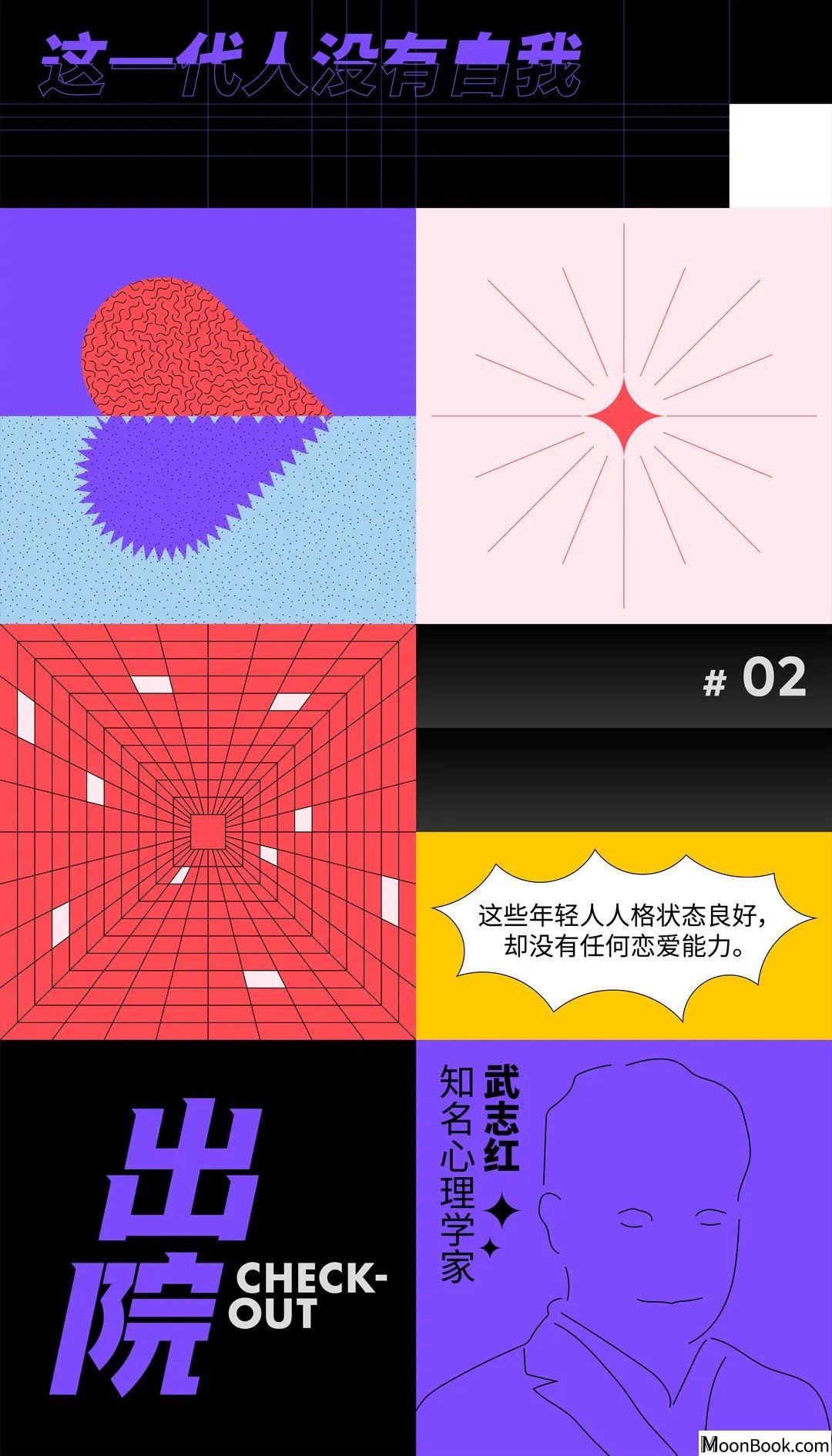

 它越不被重视,如今的大学就越可悲
它越不被重视,如今的大学就越可悲